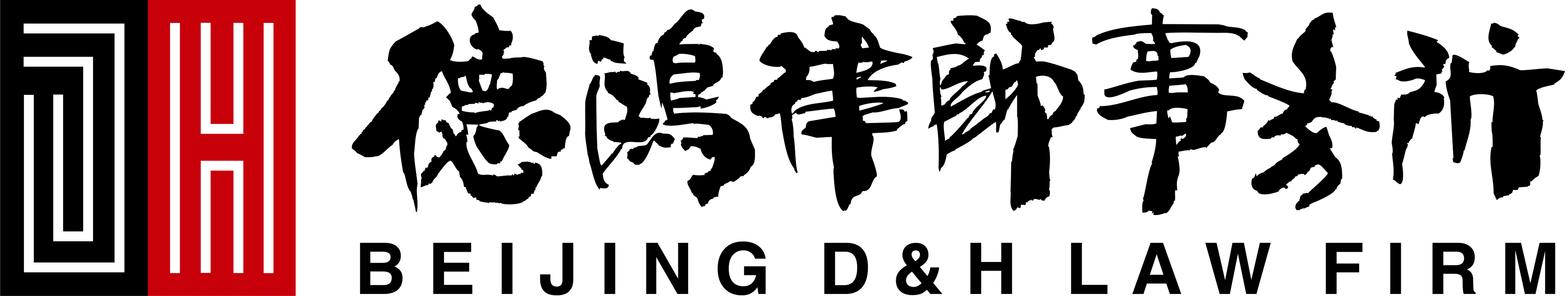前一段时期,包头市稀土高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人王永明涉嫌犯罪案件期间,有被告人当庭举报出庭检察人员李书耀索贿并以此申请李书耀回避,检察人员则认为申请回避的理由不符合法定事由、建议法庭驳回回避申请,法庭随后驳回了辩护人的回避申请。再后来,由于李书耀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不可能再办理案件,也就自然“回避”了王永明案件的办理。由于李书耀事实上回避了案件的办理,大家也就不再探寻“李书耀是不是应该回避、如何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作为法律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回避”对法律问题的探讨。出庭检察人员向被告人家属索贿属于回避情形吗?辩护人申请出庭检察人员回避的,应向谁提出?检察机关有权力建议法庭驳回对出庭检察人员的回避申请吗?法庭当庭驳回对出庭检察人员回避申请的依据何在?本文旧事重提,并无炒剩饭之意,旨在对上述问题予以简单梳理。
一、申请出庭检察人员回避、应当向谁提出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人员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检察长的回避由检察委员会决定。一般而言,对检察人员的回避申请也应当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但是,申请出庭检察人员回避的问题稍微复杂或者特殊一些,因为在开庭(不论是一审、二审、再审)这个特殊阶段,控(检)、辩、审三方已经通过出席法庭的公开工作方式在各种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会影响其他两方的工作,进而影响庭审活动的推进;同时,庭审活动是由法庭主导、指挥推进的,出庭人员都有义务服从法庭的安排。因此,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如果申请出庭检察人员回避的,应当向法庭提出,而不是向人民检察院或者出庭检察人员提出,以保证庭审活动的有序安排。
二、法庭和出庭检察人员如何处理申请出庭检察人员回避的事项
在这个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
《解释》第3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回避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休庭,并通知人民检察院。”
《规则》第28条规定:“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向法庭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回避的,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后,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回避或者驳回申请的决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应当建议法庭当庭驳回。”
《解释》和《规则》的主要区别在于,按照《规则》第28条规定,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如果被告人或辩护人向法庭申请出庭检察人员回避的,出庭检察人员“可以”自行判断申请事由是不是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9条、第30条规定的回避情形;如果认为不属于的,就“应当”建议法庭当庭驳回回避申请。但是,《解释》第31条并没有顺着《规则》第28条就“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建议法庭当庭驳回”后法庭如何处理作出规定,只是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决定休庭,并通知人民检察院。”按照《解释》的规定,不论出庭检察人员是不是建议法庭驳回回避申请,都不影响法庭最初的唯一处理方式“决定休庭并通知人民检察院。”
《解释》第31条规定和《规则》第28条规定之所以存在这种“微妙”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司法机关对法律权限的尊重、对解决司法实际问题的渴求。因为,出庭检察人员如果认为回避申请无据而“建议法庭驳回当事人回避申请”后,法庭假如真的驳回了辩护人的回避申请,那回避申请“本身”在法律意义上也就不存在了,对检察机关而言也就是不必要审查出庭检察人员是否应当回避的问题了,既没有违背“检察人员的回避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法定权限,又可以使庭审得以继续推进,因此《规则》第28条的规定确实是下了苦心。但是,如果法庭真的驳回了对出庭检察人员的回避申请,那就意味着法庭认为该申请不成立,这样事实上就造成了由法庭审查出庭检察人员是否应该回避的问题。所以,《解释》也没有越雷池一步。但是,这样的“微妙”规定也为个案争议打下来伏笔。
三、《规则》第28条的规定是“被申请者”自行裁决对自己的申请吗?
很多人对《规则》第28条关于出庭检察人员如果认为回避情形不符合法定情形、应当建议法庭当庭驳回的规定持反对意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庭检察人员本是被申请回避的“被申请人”,却直接判断申请事由是否属于法定事由、且认为如果不属于法定事由的就建议法庭驳回,是直接当了“裁判者”,因此不妥。如果仅从字面看,《规则》第28条确实可能给人一种由出庭检察人员自我判断申请事由是否有法律依据、由被申请人自行断案的感觉。但是“建议法庭当庭驳回”毕竟只是一直建议,在程序上和实体上都不是终结性的处理结论,如果把出庭检察人员“建议法庭当庭驳回”视为自己对回避申请的一种抗辩权利,也未尝不可。不能说有人申请出庭检察人员回避了,出庭检察人员连申辩机会都没有,即使是在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人员是否回避的问题时,被申请回避的检察人员同意也可以抗辩、提出自己不属于回避情形的意见。因此,本人认为对本条不必过分解读。
四、出庭检察人员向被告人家属索贿属于回避情形吗?
同是回避的情形,刑事诉讼法第29条和第30条规定的主要区别是: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的情形属于办案人员与案件之间“自然”形成的、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办理的情形;而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的情形则属于办案人员“人为”违背法律规定或者职业要求、形成的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办理的情形。
如果检察人员确实实施了向被告人家属索要贿赂的行为,无论其是否得逞,其要么是可能徇私舞弊、要么是可能怀恨在心,从理论上都可能影响其公正办理案件,因此毫无疑问应当属于回避情形,否则就违背了设置回避制度的初衷。
五、王永明案件中“出庭检察人员回避事项的处理方式”分析
被告人当庭举报出庭检察人员索贿并据此申请出庭检察人员回避,当时检察院建议驳回的理由并不是其认为索贿不属于回避情形,而是认为被告人举报出庭检察人员索贿,只是当事人的一面之词,不能以当事人的一面之词作为决定回避的依据。这个理由乍似成立,其实不然。因为无论当事人以任何理由申请办案人员回避,在其提出回避申请时从程序上看都是“一面之词”,哪怕最终查证属实。如果启动回避的审查必须以有权机关已经作出相应决定作为依据,那就完全违背了设立回避制度的初衷,甚至是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绝大部分案件根据启动不了“回避”审查程序。因此,只要当事人申请办案人员回避、且提供一定线索的(本案中提供了索贿录音),就应该让办案人员暂时停止案件的办理,待正式决定作出后再确定该办案人员是否回避。刑事诉讼法也是按照这个原则规定回避制度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言外之意,在接到对侦查人员以外的其他办案人员的回避申请后、在回避决定作出前,其他办案人员事实上是“回避”案件办理的。笔者认为王永明案件中建议驳回回避申请的实体理由不能成立。
那么,出庭的检察人员有权利建议法庭驳回当事人的回避申请吗?前面已经分析,《规则》第28条确有如此规定。因此,我们可以从《立法法》的角度分析该规定没有上位法依据,但是却不能认为办理案件的检察人员行为无据。作为一名律师,我们虽然对限制辩护人权利的现象极为愤慨,但也不能任凭情绪影响自己的法律判断,以防授人以柄。不过笔者需要声明的是,我虽然认为出庭检察人员建议合议庭驳回申请有《规则》第28条作为依据,但并不表明本人赞成出庭检察人员采取这种方式,“可为”与“该为”并不等同,对于“权力”的行使还真不能见缝插针、淋漓尽致。
至于在出庭检察人员建议法庭当庭驳回回避申请后,法庭还真的驳回了回避申请,笔者认为法庭的做法没有依据。因此这种情况下,无论出庭检察人员是否建议法庭驳回回避申请,法庭只能按照《解释》第31条的规定宣布休庭,并通知人民检察院。
六、结论